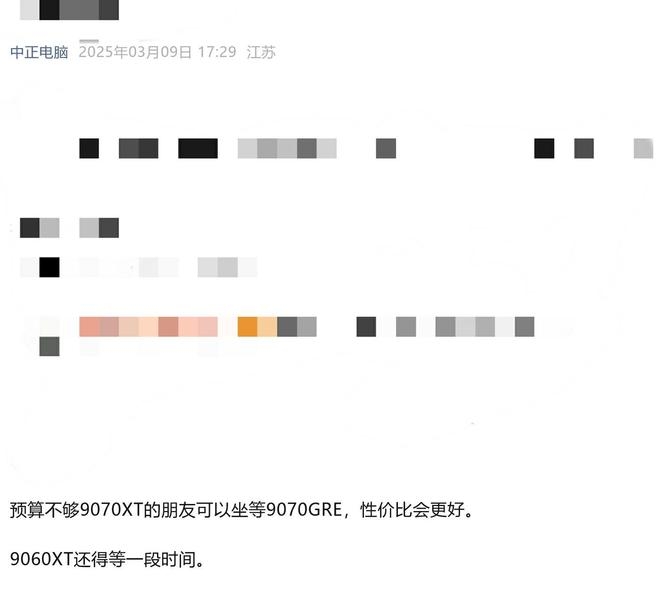出国30多年的老邻居小白姐姐回上海卖老洋房并来“我”家吃饭的故事。文中穿插了“我”儿时与小白姐姐一起挖野菜的回忆,以及青春期的一些饮食经历,最后通过小白姐姐对马兰头味道的评价,引发了对消逝美味的感慨。


近日,有一则消息让我颇为触动。出国已30多年的老邻居小白姐姐要回上海了,她打算卖掉自家的老洋房,并且还顺道要来我家吃顿饭。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按照以往的习惯,早早地就前往菜场准备食材。我心里琢磨着,怎么也得找些拿得出手的东西来招待她。
在菜场里逛着,我瞧见一个身着农妇装扮的菜贩正在叫卖野生马兰头。我赶忙跑过去一看,哪是什么野生的呀,那马兰头的杆子又细又嫩,明摆着就是大棚种植的货。真正的野生马兰头和野荠菜,它们的样子是很短很粗的,要是把它们剁碎了,那可是奇香扑鼻。不过,口感上会略微有点涩,但要是加上点麻油,那涩味就全消了,只剩下那股清新的香气。
把时间拉回到40年前,那个时候上海现在的内环线外基本全是农田。我家就位于被农田包围着的上海师范学院的东部。当时学校住房紧张,根本没有多余的房子来改善教师的居住条件。我的父亲作为外语系的青年骨干教师,也仅仅只分到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住着我、妹妹、妈妈和爸爸四个人。屋里除了一张床和几个凳子之外,几乎是家徒四壁。
小白姐姐比我大十来岁,就住在我家隔壁。她的妈妈刘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前电影资本家的女儿,她的嫂子还是王丹凤呢。小白姐姐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十来岁了,长得十分漂亮。她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带上我和妹妹,提着小篮子,到师院后面农田的田埂上去挖野生马兰头和荠菜。有时候,下过雨之后,草地上还会冒出很像木耳的地耳,吃起来味道特别鲜。要是在春天的时候,师院里的竹林还会有细细的竹笋。只不过学校不让挖,我们只能趁着晚上偷偷去,扯下几根后就拔腿跑。刘老师有一瓶珍藏的麻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可是稀罕物。我妈把马兰头剁碎后,只要喊一声刘老师,她就会小心翼翼地跑过来滴上三滴麻油。那时候,能吃上这样一顿饭,对我们家来说就算是打牙祭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十几岁,身体正处于快速生长阶段,可营养却跟不上,饥饿感也就成了我少年时代记忆的背景。
那个时候,我在校广播台当播音员,和另外一个女生一起被市里面广播台的学生节目选中,每个星期都要到市里面录一档节目。每次录完节目回学校,食堂都已经关门了,学校破例允许我们到校外买吃的。学校后门的广灵四路上有个点心店,这也就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也不知道是因为饿得厉害,还是那里的小馄饨真的太好吃了,每次我几乎一分钟内就能把一碗小馄饨全部吃完,然后等着那个女生吃。女生吃到最后几个的时候,总会说:“我吃不了那么多,你帮我吃掉几个。”我也从来不客气,呼噜呼噜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上海人逐渐摆脱贫困的那些年,正好是我的青春期,父母也有了些许的稿费收入,我的零花钱也有了保障。我积攒了一年的钱,决定去实现儿时的梦想:吃一大碗纯的蟹黄。
我坐了一晚上的船,到了嵊泗,住进了渔民家里。东海产的梭子蟹,那可都是绝对野生的,只要两块钱一斤。我买了23个,一共花了30块钱。把蟹煮熟后,我开始剥壳挖蟹黄。可吃到第十只的时候,我却感觉自己像是在吞木屑一样。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怀疑,美味是不是一种错觉呢?因为我一直在菜场里面买菜,所以和菜佬们都很熟。他们给我搞到了一条两斤半重的野生大鲳鱼,还有两条半斤重的野生黄鱼。小白姐姐吃得特别开心,她说美国的鱼又老又腥,还是东海的鱼最好吃。说起往事,小白姐姐感慨地说,吃那么好的鱼都是差不多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
小白姐姐要卖的那套洋房,其实也就是整栋里的一间而已,最后卖了一千万元。她快七十岁了,在这里也没什么亲人了,以后估计不会再回来了。临走的时候,她凑到我耳边轻声说,今天的马兰头不是很香,和我们小时候挖的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我听了这话,一下子愣住了,心里涌起一阵酸涩。
本文通过讲述小白姐姐回沪卖洋房的经历,穿插了“我”儿时与她一起挖野菜、青春期的饮食故事等回忆,展现了时光的流转和生活的变迁。小白姐姐对马兰头味道的感慨,反映出那些曾经熟悉的美味已经消逝,引发了人们对过去时光和美好事物的怀念。本文总结
原创文章,作者:Edeline,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qihaozhang.com/archives/42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