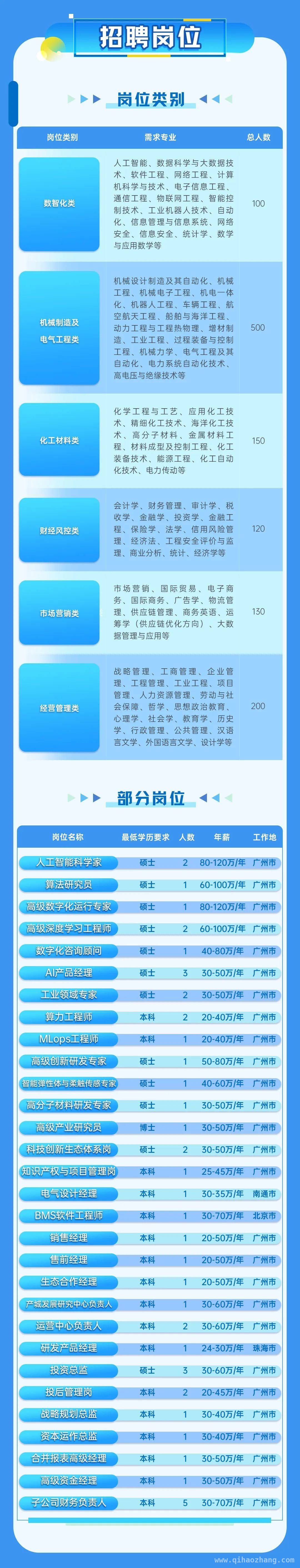本文围绕一位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母亲养育孤独症女儿树儿的经历展开,讲述了家庭在面对孤独症康复补贴政策限制、康复费用压力等困境时的挣扎,以及树儿在康复过程中的成长与进步,展现了孤独症家庭的艰难与希望。
与普通孩子相比,先天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成长进程往往较为缓慢。他们仿佛有着一套独特的思维体系,如同来自遥远的外星球,与大多数普通人的思维模式格格不入。这就要求养育他们的父母摒弃不切实际的期待,学会接纳孩子的独特性,而非试图去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闭症儿童的养育经验或许能为众多育儿家庭带来一些启示。
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出自一位孤独症儿童母亲之手。这位母亲自身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在生下这个孩子之前,她经历了一次自然流产和三次人工流产。而这第五个孩子的到来,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她在分娩前就为孩子取名“树儿”,希望女儿能安稳、正直地度过一生,不一定要成为参天大树,只要能脚踏实地、努力向上生长就好。
在树儿刚出生的前几年,她和普通孩子并无差异,甚至精力更为充沛。然而,到了五岁那年,她被确诊为轻度孤独症。和许多孤独症家庭一样,树儿的父母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逐渐开始勇敢面对。养育树儿的过程,就像西西弗推巨石,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在此期间,这位母亲还饱受“躁狂-抑郁”轮番发作的折磨。
在医生的建议下,这位母亲开始记录养育树儿的点点滴滴,近日,这些文字以《树儿:我的女儿来自星星》为名出版。她不确定写作是否能让自己获得救赎,但这至少成为了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通过每天写作,她愈发感受到女儿的珍贵,母女之间也在无形中完成了一场双向救赎。在第18个世界孤独症日,我们选取了书中“上学与康复”一节,希望通过作者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千千万万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的真实生活,让他们知道“你们并不孤单”。

### 孤独症家庭的“失败”经验孤独症早已被列入国家特病医保目录,但在全国部分省市普及刷特病医保,是2023年以后的事情。截至2022年的政策,0 – 6周岁的孤独症孩子最高可领取一年46000元的补贴。若选择缓学(一般经教育局批准可缓学一年,特殊情况可延长至两年),补贴最长可领取至八周岁,一旦上小学则自动丧失领取资格。2023年,在全国人大代表多年的呼吁和提案下,孤独症康复的部分项目被纳入医保。此外,为减轻大龄孤独症青少年家庭的经济压力,浙江省2022年推出针对低保低边家庭孤独症孩子的政策,每个孩子每月最高可享受2400元的康复补贴,一年最多领十个月,至年满十八周岁为止。
这意味着,2023年之前上小学的孤独症孩子,若想在上学后继续康复,只能自费。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康复费用在家庭支出中占比过高。“花钱买命”的潜规则在孤独症康复领域同样存在,没有补贴和医保,低收入家庭的孤独症孩子很难获得足够的康复服务。

当时政策出台后,孤独症家长群里炸开了锅。群里很多孩子已经上小学,失去了领取补贴的资格,长期的康复费用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以温州市场价为例,保持有效干预的最低频率,每月需两三千元,高密集干预至少六七千元)。家长们纷纷想办法钻政策空子,试图去社区办理低保户低边待遇。这位母亲也去社区打听,工作人员算了半天,她家不符合低保标准。尽管她家四口人中,母亲因双相情感障碍多次住院,2021年还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初期;树儿被评定为精神残疾三级;母亲自己也无业。
社区工作人员出了个主意:“你去办个残疾证,你家有两个残疾人,这边可以打擦边球帮你办低保。”母亲询问精神残疾最轻一级是否可行,工作人员表示精神残疾很难评定,一旦被评上就会被认定为丧失劳动力,让她尽力试试。母亲有三年以上的精神类药物服用史,门诊病历完整,还享受国家重大情感障碍特病医保待遇,这让她看到了评定精神残疾四级的希望。毕竟多领一本残疾证,树儿就能享受每月2400元的补贴至十八周岁。
认识的精神科医生传授了“经验”:评估前几天不要洗头,衣服和包弄脏,眼神不要太灵活,语速放慢,最好语无伦次,家属陪伴时最好当面争执、情绪爆发大哭。于是,母亲用橄榄油、酱油、马克笔等把衣服弄“脏”,一周不洗头。去医院碰到树儿的康复老师小张,小张开玩笑说她“服化道可以”。然而,评估时鉴定专家得知她没有精神病院住院史,直接表示没住过院的一律评不上,母亲的精神残疾梦就此破碎,这段经历也成了群里分享失败经验的谈资。
### 康复陪读,拼的是耐力和后劲树儿上小学后,树儿爸起初不愿意她继续去医院康复,他觉得“小时候救一下,现在这么大了,定型了,没必要再康复了,有钱就去,没钱就算了”。树儿爸的想法在孤独症家庭中并不少见,这与孤独症康复市场宣扬的“0 – 6周岁黄金干预期”焦虑有关。孤独症是一种发病原因不明的神经系统广泛性发育障碍,以目前的医疗技术无法治愈,患者的康复干预理论上需要全生命周期的支持。然而,市面上针对大龄孤独症青少年的康复机构较少,因为孩子越小家长越愿意花钱,孩子越大,干预康复难度增加,费用也偏高,有经济条件且愿意长期负担救治费用的家长并不多。
有一天,母亲接到残联负责发康复补贴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因工作统计失误,八月份多发了一个月的康复补贴,让她退还。母亲当即决定用微粒贷借款3600元退还到残联对公账户。新冠疫情三年,经济形势不好,财政紧张,政府发放补贴时断时续,许多等待补贴康复的家庭焦急万分。母亲决定,没了补贴就想办法省钱,降低康复次数,维持最低康复频率,让树儿在小学期间继续康复。因为她知道,上小学对树儿来说是新的挑战,问题行为可能会集中爆发。

康复陪伴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考验的是耐力和后劲。陪读期间,母亲全职带娃,接送时间比较自由。她问树儿:“你还想去医院见小张老师吗?”树儿回答“想”。母亲又说:“那我们约定好,不要告诉爸爸,我每周二和周四带你去见小张老师。康复费用太高,我们没钱,爸爸不想出康复费了。如果被爸爸发现你去康复,你就再也见不到小张老师了。”树儿答应“不和爸爸说,见小张老师”。在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上,树儿很聪明,严格保守秘密,一次也没说漏嘴。二年级上学期,树儿有了电话手表,为防止泄露行踪,母亲经常让她故意忘带,树儿也很配合。
2023年3月,树儿的画《斯万堡的餐厅》经康复医院选送,被温州天爱公益协会看中,参与支付宝心智障碍儿守护计划的自闭儿画作公益拍卖。4月2日国际孤独症日,这幅画在支付宝蚂蚁庄园售卖,母亲笑称树儿八岁就出道做公益了。凭借这个机会,树儿获得了温州天爱公益协会的资助,每月有3150元的报销额度,而她实际每月康复费用为2000元。这意味着在受捐助合同有效期内(合同有效期一年,是否续约待定),树儿可以免费康复。不过,获得捐助的前提是母亲要和树儿一起出镜参与天爱有关孤独症公益项目的拍摄,并授权天爱在各大视频平台不打码播出。

### 究竟什么是“康复”?每周二和周四上午,树儿会在学校消失两节课。同学小非问母亲树儿去哪儿了,母亲解释说树儿去医院康复了。小非又问“康复是什么意思”,母亲说:“树儿会在医院上一对一的课,康复老师会教她语文数学知识,和她玩游戏,教社交常识规则,还会和她聊学习生活,帮助她解决上学和家里遇到的问题。”孩子们渐渐习惯了树儿的“消失”,全班都知道树儿同时上两所学校,一所是他们的小学,一所是康复中心。
树儿的新康复老师小张是一位有包容心、爱动脑筋、充满活力的老师,她是Wing的学生。在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树儿取得了巨大进步,语言行为能力达到了六周岁普通孩子的水平(她实际九周岁),会察言观色、识别情绪,能部分表达自己的感受,有较强的规则意识和社交主动性,基本能生活自理。她成为医院康复中心的成功教学案例和活动招牌,为康复中心招生做出了贡献。
自2020年开始,在Wing和小张的带领下,他们用围绕主题和自由聊两种方式对树儿进行了近一年半的训练。大约七岁半时,树儿学会了尬聊,遇到不舒服的话题会直接说“这个话题我不想说”。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树儿都会模仿康复机构的聊天模式,这让她爸和同学有时很烦恼,她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对方感受,还会重复一个话题数月,直到别人让她闭嘴。

通过和树儿聊天以及与母亲的沟通,小张老师发现了树儿在适应学校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突然抱同学、不分场合大笑、逃避学习、写作业乱写、不敢正面拒绝大人、在校脱胸罩等。树儿性早熟,母亲提前开始做性教育功课。关于内衣不适的问题,小张老师和母亲回忆起自己少女时代的感受,树儿身材遗传了母亲,胸围宽、罩杯小,买合适的文胸很难。自闭儿性羞耻感天生偏低,树儿胸部发育,全班女生只有她穿文胸,母亲担心她不穿或被看到肩带会被嘲笑。树儿反复说“×××的乳房没发育,不用穿胸罩,我的发育了,需要穿”,这表明她在努力接受规则。Wing和小张已经教了树儿两年多性教育,现在树儿已认可自己的女性生理性别,能分清男女隐私部位。小张找来乳房发育绘本、女孩生理健康纪录片和宣教视频,还提供了“胸垫一体式固定杯德绒加绒秋衣”的拼多多链接,解决了树儿冬天穿文胸的问题。
同时,母亲也发现公办学校融合教育对孤独症孩子的康复和社交能力提升很有帮助。树儿爸算了一笔账,上公办小学一年学费全免,杂费、班费、伙食费加起来不超过5000元,持残疾证还能减免餐费,每学期还有1000元助学补助金。与康复费用相比,上公办小学花费极少。而且,普校有和普通孩子相处的集体环境,这是最好的社交环境,是康复机构社交课无法替代的。
### 一场互相救赎日子一天天过去,树儿正变得越来越“普通”,用行话说就是“隐藏度越来越高”。母亲的朋友都说树儿越来越“可控”了。母亲陪读带树儿康复的过程,也是自我疗愈的过程。树儿和母亲,一个自闭,一个双相,她们互相救赎,彼此影响。母亲对树儿的祝福很简单,就是希望她少挨父母的打骂。

在小张和Wing眼里,树儿和母亲都很棒。从她们的肯定中,母亲感受到了乐观:树儿和自己的病虽然难以治愈,但都能与疾病共生。也许七年后,树儿初中毕业没学上(树儿爸不同意她上特校高中部,以她的智力考不上普高,考上职高就算奇迹),母亲可以和树儿合作,母亲当代理人,树儿成为“孤独症艺术家”,或者她们一起开一家“树屋咖啡店”。
本文通过一位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母亲养育孤独症女儿树儿的经历,展现了孤独症家庭在经济压力、康复困境等方面的艰难处境。同时,也体现了母亲的坚持与付出,以及树儿在康复过程中的成长与进步。母女之间的互相救赎,让我们看到了爱与希望的力量,也让我们更加关注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的需求。
原创文章,作者:Isaiah,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qihaozhang.com/archives/104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