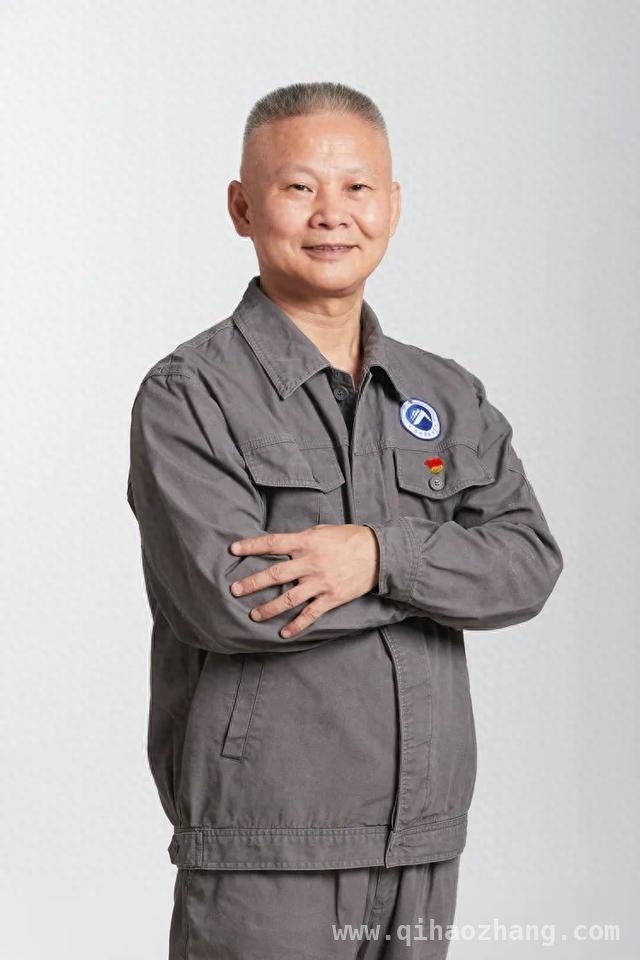本文围绕中国思想史上群己关系展开探讨,先论述儒家在集体与个体间的立场,接着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集体与个体两极的循环往复,最后深入剖析五四运动与中国旧传统的复杂关系。
悦·读

儒家的定位并非能简单归结为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它处于一种复杂的思想光谱之中,在集体与个体之间有着独特的平衡与偏向。
本篇文章约8600字,阅读大约需要26分钟。
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
余英时
此次会议聚焦于“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和个人”这一主题。我将从一个独特视角切入,把国家、社会视为“集体”一端,个人(或个体)置于另一端。如此一来,便能引出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中国传统语境中的群与己的问题。严复用“群己权界论”翻译穆勒的《自由论》,是较早触及这一问题的尝试。
不过,我无意用“集体”和“个体”的二分法去简化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际上,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都不存在纯粹的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形态。所以,本文提及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概念时,仅具有相对意义,且只是为了便于分析。
中国文化传统个人集体孰重
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现代学者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究竟更倾向于集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从古代思想史上看,中国既出现过集体主义理论,也有个体主义主张。比如,墨子的《尚同》、《商君书》中的《一教》明显属于集体主义范畴;而杨朱的《为我》、庄子的《逍遥游》以及《吕氏春秋》中的《重生》《贵己》等篇章,则代表了个体主义的一面。但自汉代以来,儒家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占据主流地位,墨家几乎销声匿迹,法家和道家虽偶有得势之时,但总体处于次要地位。儒家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
从原始教义来看,儒家秉持中庸之道,处于集体与个体的两极之间。消极方面,儒家既反对极端集体主义,也排斥极端个体主义,孟子“距杨墨”就清晰体现了这一立场。积极方面,儒家虽从孔子起就重视群体秩序,但并不抹杀个人个性。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汉以后,儒家大体沿袭这一“中庸之道”,不过,由于不断吸收其他学派思想,以及受不同时代客观形势影响,其立教重点有时偏向群体秩序,有时偏向自我认识。例如,汉代是大一统时代,群体秩序至关重要,法家韩非的三纲说便融入了儒家理论;宋明儒家的心性讨论,重点在于“为己”,这是受道、释两家(尤其是禅宗)长期挑战后的反响。即便偏向“外王之道”的王安石,也强调《论语》中“古之学者为己”的说法,他认为“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王阳明学派将心性之学发展到顶峰,宋明儒学重个体的倾向也最为明显。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个体价值的肯定
本文主旨并非探讨传统思想中的群己问题,前面的概括只是为现代思想变迁提供历史背景。若脱离这一背景,就难以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何能在短短七八十年间,在集体和个体两极之间经历两次循环。这一背景有何启示呢?我认为,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虽重视群体秩序,但仍为个体价值保留了一定空间,因此近代思想家自谭嗣同、梁启超以后,能较快冲破名教纲常束缚,建立个人自主意识。据胡适三十年代初估计,从《新民丛报》时代的梁启超到1923年,个体主义是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倾向,1923年以后,集体主义(革命或民族主义)逐渐取代了这一倾向,这也得到了近代思想运动参与者的证实。从谭嗣同的《仁学》到五四运动前后,短短二十年,个人自主解放观念就在新知识阶层中广泛传播并被接受,早期陈独秀也是提倡个体意识的重要人物。总之,中国文化传统乃至儒家内部有肯定个体的成分,这至少减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个体本位价值的抗拒。《国粹学报》作者强调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观念早已存在于中国古代经典中,虽属幼稚附会,但附会的可能源于中国传统中肯定个体价值的成分。魏晋无君论、泰州王门以及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受《国粹学报》宣扬,也能反映这一点。
然而,也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更重视群体秩序,名教纲常就是其极端表现,且与儒家关系密切。现代反传统、反儒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一点。名教纲常传统为集体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发展中,从打破旧名教束缚、要求个人自主,到接受新名教、放弃个人自主,这是第一个循环圈。如今,中国思想史正进入第二个循环圈,即打破新名教束缚,再度要求个人自主。
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复于集体个体两极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在集体与个体两极之间循环往复?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外缘因素和内在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外缘方面,主要是中国集体面临的危机,大致相当于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救亡”问题,且个体自主要求由集体危机引发。关于内在文化因素,需指出中国传统在集体与个体之间摇摆,但对两者关系缺乏清晰界定。
个人、社会、国家是西方近代概念,传统中国没有这样的划分。传统政治社会思想中,《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影响较大,看似是从“己”到“群”的推广。但《大学》是先秦晚期文献,其中“家”“国”“天下”观念与后世不同。以汉以后情况看,“齐家”难以直接过渡到“治国”;以现代情况看,“修身、齐家”属“私”领域,“治国、平天下”属“公”领域,两者存在巨大鸿沟。无论是中国传统群己关系论,还是现代西方关于个人、社会、国家的学说,中国学术思想界都未充分讨论。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在集体与个体两极徘徊:集体危机时,以“富国强兵”为现代化主要特征;个体受压抑时,又认为“个人自主”才代表现代化。
如今,西方不少思想家担忧极端个体主义(如美国代表的)对整体社会的损害,提出社群论的个人权利说,这是针对西方个体主义传统的。中国传统既非极端个体主义,也非极端集体主义,更接近社群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没有严重缺陷。如何发现传统缺陷并进行现代性调整,是重要课题。无论如何,中国传统在理论方向上不极端,兼顾群体与个体以实现平衡,是值得肯定的。
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
五四运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五四指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指这一天前后若干年内进行的文化或思想运动,其上限可追溯到1917年的文学革命,下限大致到1927年的北伐。本文所说的五四运动是广义的。以往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论,多强调其“新”的一面,尤其是接受西方思想的部分。从五四以来的历史进程看,这种强调有充分依据,因为五四在近代思想上的正面意义就在于此。至于它与中国旧传统的关系,除了反传统、反儒家外,很少有人深入探讨。本文将简要分析五四运动在思想方面与中国旧传统的关系,目的不是翻案,而是指出五四运动虽以提倡新文化为主,但仍夹杂着旧传统成分。
我们知道,五四时代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导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都出身于中国旧传统,对中国旧学问有相当造诣,且在不同领域对旧学有所贡献。他们虽许多人出国留学,受西方思想冲击,但在国外也未完全与旧学隔绝。如胡适在美国写《先秦名学史》博士论文,鲁迅与钱玄同在东京向章炳麟问学。他们青年时代受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等人思想影响较大,其中康、章两人是当时今古文经学大师。不可否认,五四运动倡导者一方面受前一时代学人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刺激,另一方面也不知不觉接受了他们对中国传统的解释。所以,分析五四与传统的复杂关系,需追溯到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康有为与章炳麟占据中心地位。从思想影响看,清末康、章并立,类似清初顾炎武与黄宗羲、中叶戴震与章学诚的“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局面,这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有趣的现象。
但近代思想史进入五四阶段时,康、章两人已落后于时代,成为保守象征。康有为提倡孔教,与“打倒孔家店”对立;章炳麟反对白话文,主张读经,与新思潮背道而驰。他们争论的今古文问题,除少数专门学者外,引不起青年知识分子兴趣。
因此,讨论五四运动思想背景的人容易忽略康、章两人与新思想运动的正面关系。实际上,深入分析会发现,康、章对新思想运动风气有开创之功。首先,今古文之争在五四时代虽思想内容过时,但激发的疑古辨伪精神在五四后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的庄严形象开始被打破。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源于早年看《国粹学报》上今古文之争文字,后来钱玄同对他说“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撕破假面目”,这一观点成为顾氏辨古史的重要武器。
不仅五四运动打破传统偶像的风气源于清末今古文之争,许多反传统议论也直接从康、章等人发展而来。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开篇称“上古茫昧无稽考”“夏殷无征,周籍已去”,甚至批评崔述《考信录》,这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起点。梁启超分析康氏《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思想界的影响,其中第三、第四点与五四新思想运动直接相关。他指出,《伪经考》质疑经典真实性,《改制考》将真经视为孔子托古之作,引发学者怀疑批评态度;康氏将孔子与诸子并列,解放“别黑白定一尊”观念,引导比较研究。
章炳麟虽与康有为今古文门户之争激烈,但在对待旧传统态度上与康氏异曲同工。钱宾四师评价章氏《国故论衡》,认为此书是新文化运动,与后来一味西化的新文化运动不同。章炳麟仅将孔子视为史家,不似康有为表面尊孔子为教主。他在日本接触日本批判儒学思想家著作,《訄书》第二篇“订孔”仿《论衡》“问孔”,对激烈反孔言论不反感。
可见章炳麟内心不认同儒家,他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影响胡适最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自序》感谢章太炎先生。蔡元培为胡书作序,指出其辨别真伪、断自老子孔子、平等对待诸子、系统研究的长处,这综合了康、章考经论子的方式。
由于章炳麟学识渊博,论学范围广,思想影响面比康有为大。五四以来推崇的非正统思想家如王充、嵇康、阮籍、颜元、戴震等,多由他进行近代评价。五四后反程朱风气也与他有关,他批评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
章炳麟虽未公开反礼教,但提倡“五朝学”,肯定钱大昕“何晏论”,对玄学清谈评价高,同情解释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之语。这与鲁迅反传统、反礼教思想渊源深厚。鲁迅1908 – 1909年在东京民报社向章炳麟问学,他听“说文解字”没记住内容,但章氏对孔子不太尊敬的言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周作人回忆章氏讲解“说文”时拿孔子开玩笑,鲁迅后来虽记不起讲“说文解字”的话,但这类话肯定记得不少。
刘半农赠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联语,鲁迅认可,这反映了五四初期的鲁迅。实际上,鲁迅爱好魏晋文章,受魏晋思想感染,章炳麟影响明显。章炳麟提倡魏晋文章,鲁迅对《嵇康集》产生浓厚兴趣,民国二年后多次校勘。鲁迅性格与孔融、嵇康相似,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为嵇、阮“毁坏礼教”罪名洗刷,认为魏晋崇奉礼教者实则毁坏礼教,不信礼教者表面毁坏实则承认礼教。鲁迅做人有“世故”一面,与嵇康细心多疑之处契合,他去世时儿子不知他是鲁迅,不知是有意效法嵇康诫子,还是性格偶合。
从鲁迅的例子能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传统的依赖深厚。当时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反传统、反礼教时会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源头找依据,因为这是他们熟悉的内容。外来新思想需附会传统已有观念才有实际意义,如言平等附会墨子兼爱,言自由附会庄生逍遥,言民约附会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这是魏晋“格义”老办法。胡适“非孝”说依据王充、孔融以来“父之于子,当有何亲”的议论。
五四时代,中国传统中非正统、反正统作品受欢迎,胡适将“整理国故”视为“新思潮的意义”一部分,可见五四与传统联系紧密。鲁迅虽讨厌“国故”,但仍做了“整理国故”工作,《小说旧闻钞》再版距他逝世仅一年多。
李文孙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理智选择西方价值,情感难舍中国旧传统,此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过于笼统。中国传统内容复杂,不能简单处理。传统中非正统、反正统成分兴起与西方价值冲击有关,但也并非完全被动。近代西方文化进入前,传统异端就有激烈偶像破坏运动,如潘用微痛斥孔庙两庑,清初颜元反程朱陆王、反训诂考证。但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未全面解体,无外来文化挑战,反传统思想未充分发展。康有为、章炳麟反传统思想受外来影响,但主要成分从清代学术演变而来。清代考证学研究使异端学说得到整理,戴震“以理杀人”之说在五四与“吃人礼教”口号合流。可见,五四运动有中国传统根源,虽无外力冲击,新文化运动可能难以发展,但本文目的是澄清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的关系。
然而,问题不止于此。五四运动发展成特殊形态,其民主与科学目标至今未充分实现,与中国传统密切相关。我曾引用弗里德里希的话,强调思想和行动涉及创造性因素及不可预料途径,思想模式很重要。林毓生先生已对传统“思想模式”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进行部分疏解,问题复杂,值得深入研究。概括地说,五四运动类似贝克分析的欧洲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摧毁旧天国后,重建的天国仍未突破旧格局。五四运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秩序,但五四以来中国人运用新观念重建的文化秩序,仍未突破传统格局。“四人帮”垮台后,知识分子反思为何中国“封建”“专制”屡经“革命”不衰,为何五四60年后民主和科学仍是追求目标。鲁迅在五四时代说读史能觉悟中国改革的紧迫性,查看五四运动旧账,更能体会鲁迅的先见之明。
本文围绕中国思想史上群己关系展开深入探讨,先阐述儒家在集体与个体间的中庸立场及随时代的偏向变化,接着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集体与个体两极的循环现象及原因,最后详细剖析五四运动与中国旧传统的复杂关系,揭示五四运动虽倡导新文化,但深受旧传统影响,且其发展形态与目标实现受传统思想模式制约,强调深入研究传统与现代思想碰撞交融的重要性。
原创文章,作者:modesty,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qihaozhang.com/archives/16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