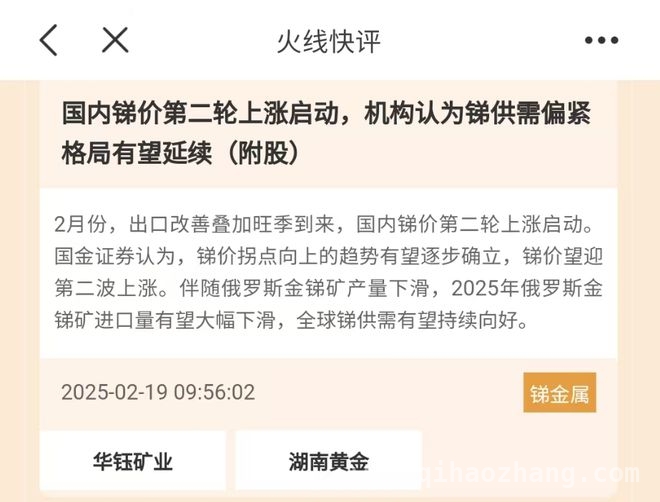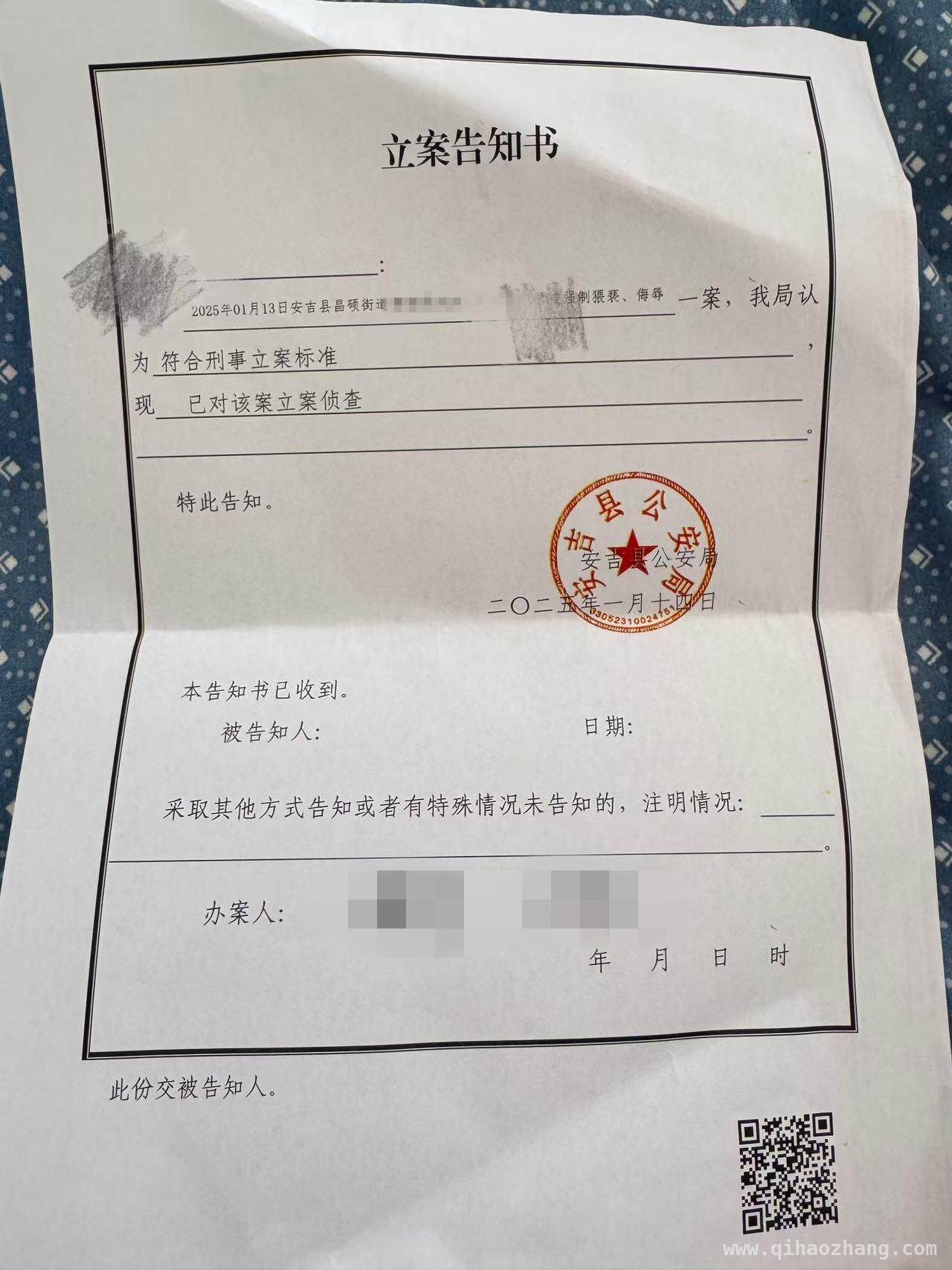作者在清明时节回到潍坊老家,详细介绍了当地插柳、上坟、打秋千、踏春等清明习俗,展现了传统节日的热闹氛围和深厚的乡土情结,同时也提及了随着社会变迁,节日内涵的变化。
又是一年清明至,清明,向来是一个让人思绪万千、感怀过往的时节。今年清明,我与家人一同回到了潍坊的老家。这个村庄,相传因战国先贤淳于髡蛰居于此而得名,带着对祖先的敬意和对往昔的怀念,我们踏上了这片熟悉又亲切的土地。站在坟地旁,看着那几株已然绽放的桃树,粉嫩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儿时的回忆、家族的过往,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插柳,是清明时节在老家上演的首开剧目。“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这句古老的俗语,承载着人们对平安和吉祥的美好期许。寒食这一日,天刚破晓,村子里的孩子们便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不约而同地换上新做或者新洗的单衣、薄鞋,手里拿着铲子或者镢头,像一群欢快的小鹿,朝着坡上奔去。清晨的风,轻柔地拂过脸颊,带着丝丝缕缕的暖意,空气中弥漫着新土的清新气息,那是大地苏醒的味道。孩子们如同灵敏的猎犬,在草丛中仔细地寻觅着两三朵老翁花的苞芽。老翁花,学名白头翁,它生长在野外,并不常见,每找到一朵,孩子们都会兴奋地欢呼起来。

接着,孩子们爬上河沿上的柳树,小心翼翼地拽下几根细长且刚出芽的柳枝。这个任务必须在太阳升起之前完成,因为在老人们的说法里,这样才会有好兆头。孩子们欢蹦乱跳地跑回家里,把老翁花芽和一小片松枝精心地绑在一起,再用细长的线系在事先挑好的一支细长顺柔的柳枝条尖上。他们一边认真地默念着“老翁花、老翁花,蝎子蚰蜒不到家”,一边将枝条的另一头插在堂屋灶上方的梁檐上。随后,把松枝和柳枝条扎成几束,插在大门口门框边,再把柳枝扎成几个圈,给院子里的羊角、狗脖子套上,自己也留一个戴在头上。最后,孩子们把特意留下的柳枝,用手轻轻回环拧一下,抽出里面嫩白的芯,做成柳哨。一时间,村子里回荡着高低长短的哨音,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节日乐章。
上坟,是清明不可或缺的传统节目。无论在城里做工的,还是嫁到外村的,只要能回来的人,都会相约一起去上坟。一般是在上午,大人和孩子成群结队,带着精心准备的供品、烧纸,扛着铁锨,纷纷朝着各家的坟地走去。烧纸的时候,人们会虔诚地给先人们念叨几句,把家里新发生的大事、好事都一一诉说,祈求先人保佑家人和顺康安。大家一定要守在跟前,看着纸钱焚烧完毕,这既是对祖先的尊敬,也是为了防止纸钱被风吹到旁处,引着枯草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敬完酒,接下来就是敬拜祖先,长辈和后辈依次叩拜。拜祭完毕后,祭品被认为是得到了祖先的祝福,众人便可以食用。最后,有的人家也会放鞭炮告别。走进墓地,除了一些悲怆的哭声和抽泣声,人们都不会大声喧哗,整个墓地笼罩着庄重肃穆的气氛。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家静静沉浸在“父母在尚有来处,父母不在只有归途”的伤绪里,感怀着亲人以往的长情,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叶落归根、离人寻根”的乡土情结,接受着敬祖孝老、珍重家人的心灵洗礼。

打秋千,是清明的经典剧目。在村子里,总有几处打秋千的地方。年景好的时候,村里会集体出人出料出力建一个特大特高的秋千。记得我们村曾经连着两三年在打麦子的场院里竖起过十多米高的大秋千,那壮观的景象,吸引了七里八村的人前来游玩。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都穿上亮颜色的衣服,把秋千当成了戏耍的舞台,在上面“争奇斗艳”。年轻的小伙子们更是见缝插针似的在秋千上“炫武展艺”。他们完成用力躬身、屈腿、下蹲、直起、挺身、扩胸这一系列连续动作,我们称之为“驱”,这是打秋千最基本的动作;当别人执绳或拖着座板将秋千荡起,就叫做“送”。秋千荡起来后,上面横梁上的两拘(拴绳的套环)会逐渐向横梁中间靠,这叫做“并拘”。按照习惯,“并拘”之后,绳子靠在一起打转容易发生危险,就要停下来让给别人。秋千上的人双手紧紧抓着吊绳,弯腰屈腿,挺胸收臀,衣袖在风中飘飘扬扬,在“驱”“送”之间,让自己越荡越高。有厉害的人,甚至能让脚踏板高过自己的头部,超过秋千竖立的最高横梁,惹得下边的人惊呼阵阵,啧啧称赞。
踏春,是清明的撒欢节目。“清明前后,种瓜种豆。”对于大人们来说,踏春意味着踏着春天的农时,开始忙活耕田犁地、春播春种的农事。而挖野菜则成了孩子们踏春的自演剧目。“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与城里孩子们的踏青春游不同,一直住在山野土村的孩子有着别样的感受。经过漫长冬天的封锁,孩子们终于能够走到田野,去寻找春天大地无私奉送的野菜,以补充寡汤寡水的食桌。“杏花落、桃花开,野茄子花开割韭菜。”除了菜园里的韭菜、菠菜、茼蒿等时令菜,田野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菜地。苦菜子连着叶和根可以蘸酱生吃,曲曲芽、婆婆丁焯水凉拌吃。还有两种特别的野菜令人难忘,一种是贼蒜,一种是鸭葱,微微辛辣的贼蒜,泛着清甜的鸭葱,滋润了孩子们的味觉。稍大一些的年轻人,已不满足于村旁的田野和矮山,他们相约着向周边更远更高的山攀爬。记得有几次,我与伙伴们走着去爬近十里路远的乔山。乔山脚下的路有三个起伏,附近的人们都叫它“三瞪眼”,每上一段坡,就要出一身汗,停下来歇一歇,瞪一次眼。经过“三瞪眼”的爬坡,再开始爬一段垂直高度三百多米的更陡坡面的山。等攀到山顶,一般人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但当他们站起来,看到远处“阡陌纵横、万千风物”的美景时,便收获了平日大不相同的光景,增添了“无限风光在高处”的心气,更是催生了自己“路修远以求索”的探问。
如今,村里平常在家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至多是在农忙时回家帮把手,然后又返回城里。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城乡的变迁,寒食节已经不再是现在孩子们所惦念的,清明节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看着逐渐老去的村庄,邻里之间难有年轻人的身影,不禁让人感慨:老村乡居多近暮,邻家难有少相遇;新人谁记寒食景,春山清明几归赴?
本文通过回忆清明时节在潍坊老家的插柳、上坟、打秋千、踏春等传统习俗,展现了浓厚的乡土风情和家族亲情。但随着社会发展,年轻人逐渐离开乡村,传统节日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表达了对传统习俗传承的担忧和对乡村变迁的感慨。
原创文章,作者:Isaiah,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qihaozhang.com/archives/12425.html